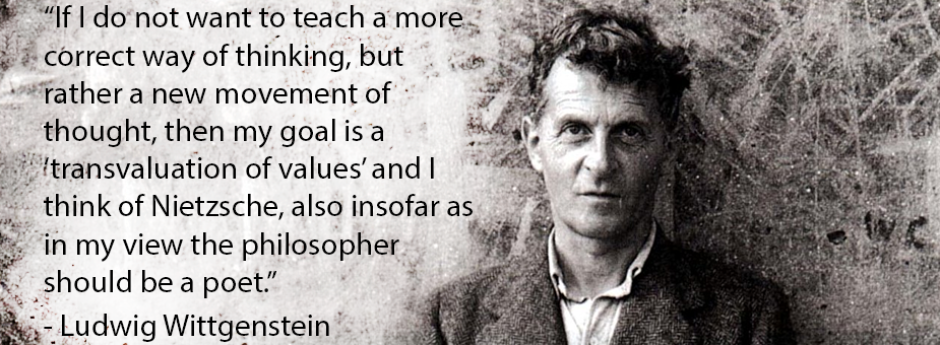余光中認為,一個夠資格的批評家應具備下列四種條件。雖然這是針對文學,但我想,倘若下述文學領域的名稱改成其他領域,應該也都適用:
(一)他必須精通(至少一種)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識。必須如此,他才能不仰賴別人的翻譯。如果一個批評家要從中譯本去認識莎士比亞,或從日文論述中去研究里爾克,那將是徒勞。(二)他必須精通該國的文學史。這就是說,他必須對該國的文學具有歷史的透視。必如此,他對於某一作家的認識始能免於孤立絕緣的真空狀態。必如此,他才能見出拜倫和頗普的關係,或是康明思受莎士比亞的影響。批評家必須胸有森林,始能說出目中的樹有多高多大。(三)批評家必須學有所專。他要介紹但丁,必先懂得耶教;要評述雪萊,最好先讀柏拉圖;要攻擊傑佛斯,不能對於尼采一無所知。一位批評家不解清教為何物而要喋喋不休地談論霍桑的小說,是不可思議的。(四)他必須是個相當傑出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應該別具一種風格,而不得僅為表達思想之工具。我們很難想像,一位筆鋒遲鈍的批評家如何介紹王爾德,也無法相信,一個四平八穩的庸才攫住康明思的文字遊戲。一篇上乘的批評文章,警語成串,靈感閃爍,自身就是一個欣賞的對象。誰耐煩去看資料的堆積和教條的練習?
由於近來有些畫家、作曲家、詩人準備發起一項文藝復興運動,而我在《文星》上寫了幾篇試探性的短文,遂引起文藝界某些人士的關切。一種意見在提出後,有了反應,無論如何總是好事,某些反應是善意的,例如方以直先生在《征信新聞》上發表的文章。我們深為這種友情所鼓舞。
但是另有一些反應,雖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有人說,余光中要“回國”了,他那條現代詩的路走不通了,終於要向傳統投降了。有些人說,在詩中用幾個典故,或是發懷古之幽思,不得謂之認識傳統。對於這些見解,我無意浪費藍墨水,作無益的爭辯。不錯,我是要回來的,正如劉國松、楊英風、許常惠要回來一樣,可是我並不準備回來打麻將,或是開同鄉會,或是躲到漢嘉陵闕裡去看西風殘照。我只是不甘心做孝子,也不放心做浪子,只是嘗試尋找,看有沒有做第三種子弟的可能。至於孝子、浪子,甚至“父老們”高興不高興,我是不在乎的。
真正的“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是一念懷鄉,就可以即時命駕的。方以直先生說,他願意在松山機場歡迎浪子回來。他的話很有風趣,可是他的原意,我想,不會是指那些在海關檢查時被人發現腦中空空囊中也空空的赤貧歸僑吧。
“回來”並不意味著放棄“西化”。“五四”迄今,近半世紀,“西化”的努力仍然不夠,其成就仍然可憐。最值得注意的是:浪子們儘管高呼“全盤西化”,對於西洋的現代文藝,並無若何介紹。“回來”與“西化”是達到此一目的之手段之一。因此,如果有人誤認我們要放棄對於西洋文藝的介紹,那是很不幸的。
要介紹西洋文藝,尤其是文學,翻譯是最直接可靠的手段。翻譯對文學的貢獻,遠比我們想像的偉大。在中世紀的歐洲,許多國家只有翻譯文學,而無創作文學。影響英國文學最大的一部作品,便是 1611 年英譯本的《聖經》許多不能直接閱讀原文的作家,如莎士比亞、班揚、濟慈,都自翻譯作品吸收了豐富的營養。
然而翻譯是一種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種很難的藝術。大翻譯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種能力,將兩種並非一見鍾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對佳偶。將外文譯成中文,需要該種外文的理解力和中文的表達力。許多“翻譯家”空負盛名,如果將他們的翻譯拿來和原文仔細對照,其錯誤之多,其錯誤之牛頭不對馬嘴,是驚人的。例如某位“名家”,在譯培根散文時,就將 divers faces(各種面容)譯成“潛水夫的臉”。又如某詩人,便將 dropping slow 譯成“落雪”,復將浩司曼詩中的“時態”整個看錯。原是過去與現在的對照,給看成都是現在的描寫,簡直荒唐。創作的高下,容有見仁見智之差。翻譯則除了高下之差,尚有正誤之分,苟無充分把握,實在不必自誤誤人。
翻譯之外,尚有批評。批評之難尤甚於翻譯。我們可說某篇翻譯是正確的翻譯,但無法有把握地說某篇批評是正確的批評。創作可以憑“才氣”,批評卻需要大量的學問和灼見。梁實秋先生曾說,我們能有“天才的作家”,但不能有“天才的批評家”。作家可以有所偏好,走自己的窄路;批評家必須視野廣闊,始能綜觀全局,有輕重,有比例。換言之,批評家必須兼諳各家各派的風格,他必須博覽典籍。台灣文壇的學術水準甚低,因此我們的文學批評也最貧乏。
要做一個夠資格的批評家,我以為應具下列各種起碼的條件:
(一)他必須精通(至少一種)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識。必須如此,他才能不仰賴別人的翻譯。如果一個批評家要從中譯本去認識莎士比亞,或從日文論述中去研究里爾克,那將是徒勞。(二)他必須精通該國的文學史。這就是說,他必須對該國的文學具有歷史的透視。必如此,他對於某一作家的認識始能免於孤立絕緣的真空狀態。必如此,他才能見出拜倫和頗普的關係,或是康明思受莎士比亞的影響。批評家必須胸有森林,始能說出目中的樹有多高多大。(三)批評家必須學有所專。他要介紹但丁,必先懂得耶教;要評述雪萊,最好先讀柏拉圖;要攻擊傑佛斯,不能對於尼采一無所知。一位批評家不解清教為何物而要喋喋不休地談論霍桑的小說,是不可思議的。(四)他必須是個相當傑出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應該別具一種風格,而不得僅為表達思想之工具。我們很難想像,一位筆鋒遲鈍的批評家如何介紹王爾德,也無法相信,一個四平八穩的庸才攫住康明思的文字遊戲。一篇上乘的批評文章,警語成串,靈感閃爍,自身就是一個欣賞的對象。誰耐煩去看資料的堆積和教條的練習?
我不敢武斷地說,台灣的創作不如西洋,但我敢說,我們的翻譯和批評實在太少也太差了。要提高我們的文學創作水準和作家一般的修養,我們需要大量而優秀的翻譯家和批評家。至少在往後的五年內,我們應朝這方面去努力。